菠萝首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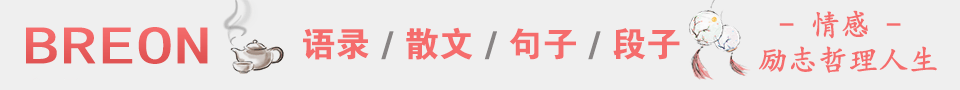
最爱我的你
归档日期:11-13 文本归类:精选短文 文章编辑:菠萝语录

图/电影《夜莺》
文/JJ
来自读者投稿
夜里一场滂沱大雨,雷电交加,接着收到了区域性洪涝的手机短信,然后就突然断了电。这样的情况实属难得。那一刻,只觉得自己身处的世界黑漆漆的一片,身边的一切都被黑色给吞噬了。这个嘈杂的世界,突然就随着灯光的消失肃穆起来,就算闪电依旧噼里啪啦,雷声依旧此起彼伏,整个世界在我看来却是安静平和的。
我借着手机屏幕的光亮,找出很久没有用过的蜡烛和打火机,用打火机点着蜡烛,然后看红蓝色的火苗在一片黑里自顾自的欢快地跳跃着,一片昏黄的光亮在房子里慢慢地舒展开来,一圈一圈地发散出去。眼前的景象突然变得陌生又熟悉,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慢慢的,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,那个人的样子既模糊又亲切,在跳跃的烛光里,他带着我回到了从前,很久以前的从前。
在我的记忆里,一直存有这么一个模糊的画面,是被黑暗笼罩着的。那个画面里有一个大台门,一间大大的堂屋,角落里放着一张八仙桌,昏暗的橘黄色的光,老旧的摆设,黑簇簇的镂花背景,堂屋的中间横着一口崭新的木头棺材,里面很认真的平躺着一个人,我看不清那个人的容貌,却知道他穿戴整整齐齐,表情一丝不苟。那个画面里还有很多其他成年人,也看不清他们的容貌,貌似七大姑八大婆大家伙儿都到齐了,大家都忙忙碌碌地肃穆着走来走去。那个画面里还有一个剪着蘑菇头的小姑娘,五岁光景,她好奇地睁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,默默地走到那个平躺的人跟前,用右手的食指轻轻的滑过他的脸庞。
那个躺着的人是我爷爷,那一年我五岁。
不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没有,在我的记忆里,应该是没有。因为我隐约记得那天晚上,有人千方百计地鼓动我放声大哭,说那样爷爷上路的时候能够听到,可以带着我们的爱安心上路。想来,一定是我当时木然、不知所措的表情委实让人着急。如果一定要我描述一下当时的心情,我能够想到的就是爷爷睡着了,家里人很多,很热闹。而我喜欢热闹,跟过年似的。
我所记得爷爷与我之间的关系,非常零星,而且是呈点状,不连续的,又如萤火虫尾巴上的光亮,跳跃着,闪烁着,忽隐忽现的。就好像我是记得这么一个人的,但是又不是很确信。然而,每次长辈们说起爷爷和我之间的事,内容大体相同,描述都很一致,大家说话的语气里都飘着些许羡慕,些许妒忌,还有些许惋惜。那些描述,可以归纳为一句话:万千宠爱集一身。每次说到最后,长辈们总会以一句“可惜他走得太早”来结尾。
他,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最爱我的人。他,也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给我死亡概念的人。虽然我对这两点都没有深刻的体会。
关于爷爷奶奶之间的爱情故事,我不甚了解。只听说他们是邻居,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于江南小镇喜结良缘,然后就陆陆续续地有了我姑姑,伯伯和我爸。不记得姑姑的乳名是什么了,那个年代女孩子家一般是不受重视的。我伯伯的乳名是“路见”,听说是为了纪念奶奶和爷爷在逃难中的某一次不期而遇,我爸的乳名是“宜昌”,听说那是他的出生地,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湖北宜昌。
路见,宜昌,是他们当时颠沛流离生活的见证。
后来,因为有一技之长,爷爷招工去了香港的一家纺织厂,做机器维修,从此和奶奶长期两地分居。奶奶是个不识字却识大体的老式家庭妇女,留在家乡含辛茹苦养育三个孩子,而爷爷,作为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,则在异地他乡省吃俭用,不断地把不菲的收入汇给奶奶。而我爸是家里的小儿子,得到了特别的宠爱。所以,听我爸说起他童年的事,常常可以听到小笼包,狗肉,羊肉之类的字眼。这些字眼,对于那一代人来说,是奢侈的,于我爸,却是稀松平常的事。
爷爷一直在香港工作到退休,才告老还乡,和奶奶团聚。爷爷回到家乡的时候,姑姑已经有了三个儿子,伯伯家也有两个儿子。虽然我爸妈通过上大学最后留在了省会大城市里,我却是在爷爷奶奶家乡的小镇上出生的。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缘故,我的出生,给爷爷带去了极大的欣喜,我成了他的掌上明珠。
爷爷奶奶的家在一个弄堂里。那个弄堂,有着狭小的弄堂口,走进去了,反倒变得越来越开阔。相较于弄堂里的其他房子,这是一个有着高高的围墙,高高的石阶,和一扇厚重的棕色木门的大院子,就在弄堂的半中央,大家称之为“大台门”。大台门里住着七八户人家,每家都是两层楼的木头老房子,有着那种上楼会吱呀吱呀作响的楼梯,爷爷奶奶就住在大台门里。这些房子围成正方形一圈,中间是一块公共区域,那里种着一些树,我记得的有枣树和石榴树,以及其它的一些花花草草,更多时候,那块地是大家用来洗衣服,泼淘米水,泼洗脚水的地方。
其实,听长辈们说起爷爷和我的过往,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件事。可是这些事,对于一个有着五个孙子和外甥的老头子来说,在当时显得非同寻常。正是因为他把全部的热情和爱都偏执地给了我这个姑娘儿,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,这种行为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,以至于让大家一直记得这个奇怪的老头子。
听长辈们说,夏天的晚上,老头子喜欢拉一张躺式藤椅放在自家门口,自己胖胖的身子往藤椅上一躺,摇着蒲扇,等着年幼的我爬到他的肚皮上,坐定,然后任由我pia,pia地用力拍打他的大肚皮,嘴里用方言使劲喊着当时最流行的那句口号:打倒日本佬!因为在故乡方言中,日和十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发音,年幼的我一直以为我喊的是打倒十本佬,依我的逻辑,既然是十,那么下面就可以以此类推,是二十,三十,于是我往往会接着喊:打倒廿本佬,打倒三十本佬……一般到三十我就数不下去了,而他还是摇着蒲扇,一边帮我驱赶着蚊子,一边呵呵呵地笑着说,打得好,打得好……然后又从头来一遍。爷孙俩傻乎乎的乐此不疲,也成为夏日大台门里的一道风景。
也听长辈们说,老头子是个没事找事的老顽童,最喜欢逗我玩。有一次我正捧着饭碗认真地吃饭,他坐在一旁,突然抬眼,一本正经地跟我说:看,你的饭碗下面是漏的……我低头一看,看到座位下面黑黑的地上掉着白白的饭米粒,于是我就把饭碗整个地翻过来想看个究竟,可想而知,一下子整碗饭菜全都倒在了地上,我先是大哭,招来了奶奶,继而大怒,手里拿着空碗,追着他,要打他,而他就跑,一个乐呵呵的大胖子在大台门的院子里跑得气喘吁吁的。奶奶则站在屋门口生气地骂他是个老不正经的东西,都不让人吃一顿安稳饭。
上一篇:姑娘请不要再绑架自己
下一篇:日语好是怎样一种体验
- 本站最新....






